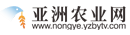■本报记者 陈彬 实习生 刘聪儿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很快,赵晶(化名)可能会迎来一批有些“特殊”的新同事。
作为国内某高校的专职辅导员,赵晶当初求职时,学校直接和她签订了工作合同并给予编制。但不久前,该校公布的辅导员招聘启事却宣称,此次录取辅导员的聘期分为两段,前半段按照非实名人员聘用,期满进行考核,通过者进入后半段,并办理事业编制;不合格者不再续聘。这种形式十分类似于目前在聘用高校教师时采用的“非升即走”制度。
“这将是学校第一批‘非升即走’的辅导员。”赵晶说。而据《中国科学报》了解,今年除赵晶所在高校外,包括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南方科技大学等在内的多所国内高校均实行了类似制度。
近年来,因为拥有更多发展途径,又可以直接“入编”,辅导员岗位成为求职者眼中的“香饽饽”,这让高校中其他岗位的一些教师“羡慕嫉妒恨”。而随着“非升即走”制度的实施,未来辅导员岗位还“香”吗?
“他们和我们没什么不同”
严格意义上说,“非升即走”制度并不是今年才在我国高校辅导员群体中出现的。比如国内某地方高校辅导员刘江(化名)便告诉《中国科学报》,他所在的学校早在两年前就已存在一批“非升即走”的辅导员。
“是那些以博士学位入职,同时想走思想政治教育序列的辅导员。”他说,如果这些辅导员5年内不能评上副教授,就面临“走”的命运。“这样的制度两年前就已经开始实施了。”
刘江解释说,目前国内高校辅导员实行的是“双线晋级”政策,即辅导员拥有“教师”和“管理者”双重身份。相应的,其发展途径也有两条。
以刘江为例,走行政管理职称序列的他,目前的职称为管理七级。未来,他有可能进入学校的各种行政管理岗位。而如果选择走专业技术职称序列,他则可以成为讲师乃至副教授、教授,其身份也会变为思政类等相关课程的授课老师。“不过一般情况下,绝大部分辅导员还是走管理序列,最终能评为副教授的还是少数。”
尽管如此,多样化的职业发展途径已足以令校内其他行政岗位人员称羡。“毕竟诸如财务等很多校内行政岗位,其专业门槛还是比较高的。相比之下,辅导员的专业门槛较低,发展途径却更多。”刘江说。
既拥有更多发展途径,又可以在入职之初拿到编制,这样的“待遇”使得辅导员岗位成了近年来很多高校毕业生眼中的“香饽饽”。
2022年3月,教育部在新闻发布会上透露,截至当年,全国高校专兼职辅导员达24.08万人,比2019年增加了约5.2万人。
赵晶便是这5.2万人中的一员。
当初择业时,赵晶曾在“辅导员”和“选调生”之间犹豫许久,最终还是选择了前者。“主要原因还是出于对母校的感情,但稳定也是一个考虑因素。”当年与她同时竞争这一岗位的人数超过了6000,最终如愿者不超过50人,名副其实的百里挑一。
受访时,南京大学陶行知教师教育学院副院长操太圣直言,正是目前辅导员岗位“一岗难求”的局面,使之成为完全的买方市场,高校在几乎没有招聘压力的情况下,自然会变得挑剔。近年来辅导员整体学历水平的提升,以及在辅导员招聘中出现的类似“非升即走”规定等,均是这一大背景的具体投射。
此外,操太圣表示,高校之所以在辅导员群体中推行“非升即走”,也可能与宏观层面的高校人事改革有关。“因为经过这些年的推动,‘非升即走’在高校教师中已是大势所趋。”此时高校很容易产生将类似制度向校内其他群体推广的想法,而基数庞大又不愁招不到人的辅导员群体自然成了最好的“实验对象”。
值得注意的是,对于教师,尤其是青年教师而言,“非升即走”所带来的职业压力不言而喻,甚至使一些高校老师“谈虎色变”。然而,当这份压力“转移”到辅导员群体时,情况却似乎有了很大不同。
比如,当被问及对未来那些需要“非升即走”的新同事是否会“心生怜悯”时,赵晶直言“不会,他们应该和我们没什么不同”。刘江也表示,这项制度给辅导员带来的压力“应该不会太大”。
类似的回答几乎成了受访辅导员在被问及相关问题时的“标准答案”,似乎对于“非升即走”这项有可能影响其职业生涯的制度,作为“实验对象”的辅导员们仍然处于“无感”的状态。
拥有如此心态,这些辅导员“底气”何在?
一边“确保入编”,一边“非升即走”
在回答这一问题之前,有必要对目前高校辅导员聘用及考核情况做一了解。
纵观这两年高校对辅导员的招聘情况,赵晶所在学校采取的措施并非个例。比如,早在2021年,武汉理工大学对新聘学生辅导员的考核实施方案中,便提到辅导员试用期满后,考评和聘期考核等分为合格和不合格。新聘用学生辅导员中期考核优秀或聘期考核合格的,即可转入事业编制。考核不合格人员,学校将与之解除聘用合同。
今年,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对辅导员采取合约聘期制进行管理。预聘采取“3年+3年”的合约聘期制,长聘采取无固定期限的合约聘期制。
南方科技大学在今年的学生辅导员招聘启事中明确,考核通过者采用预聘制方式聘用。预聘制聘期为6到12个月,期满经考核合格者,按流程转为校内职员并纳入学校员额编制管理。
此外,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云南民族大学等高校在今年辅导员的招聘公告中,均明确招聘人员按照预聘制方式聘用。
此前,高校辅导员并不是这样招聘的。
王兴(化名)在2013年成为一名专职辅导员。与当时国内几乎所有高校辅导员一样,在经过一轮“笔试+面试”的考核后,成功“突围”的他与学校直接签订了工作合同。“当年学校招了20个人,总成绩居前10名的直接‘入编’,后10名两年后经过考核再安排‘入编’。”
现在看来,“后10名”的遭遇与如今的“非升即走”有些类似,但王兴却直言两者有明显不同。
“之所以给‘后10名’一个‘考核期’,学校并非出于,或者说并非主要出于考核目的,而仅仅是因为一时间拿不出那么多编制。”王兴说。两年后,这10名辅导员全部通过考核,顺利“入编”。
刘江也曾有过类似经历。
在工作的前两年,刘江一直都是人事代理关系。但在他几经努力获得编制后,该校所有新进辅导员只要入职便可以直接拿到编制。
这一现象并不罕见,因为几乎就在高校开始对辅导员考核制度进行调整的同时,各级政府频频发文,要求确保辅导员全部“入编”。
仅在今年,教育部思想政治工作司就在其发布的2023年工作要点中提到要落实辅导员岗位编制。在地方层面,江西省今年发文,明确公办高校专职辅导员必须在编制内配备;陕西省教育厅表示为满编超编高校争取更多周转池计划,督导落实高校专职辅导员和思政课教师配备入编……
正是有了“确保入编”的承诺,辅导员岗位的优越性才再次被提升,并在一定程度上为辅导员“非升即走”的推行提供了政策支持。
标准是什么
与很多新生事物一样,辅导员“非升即走”制度虽然只是在小范围内实施,但已经引发了一些争议,其中最主要的争议点是如何制定标准。
正如长期关注教育政策相关问题的江南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田贤鹏所说,“判断辅导员是否达到‘非升即走’标准的依据是该政策能否顺利实施的关键”。
他解释说,高校教师与辅导员的工作评判标准有很大不同,前者标准相对明确且更容易操作,主要依据教师的科研成果和教学成果,尽管在具体的实施上存在一些争议,但还是相对规范的。“相比之下,辅导员的评价标准则要模糊得多。”
以赵晶为例,刚刚过去的7月,尚在暑假中的她几乎没有休息,而是带领学生进行了长时间的暑期社会实践,几天前才刚刚返校。即便是正常的学期中,她周一到周五也经常要到晚上八九点才下班。“周末主要参加一些学生活动,还要组织学生开会或参加大型活动的筹备工作……当然,这些还属于比较正常的情况,如果有突发事件就另说了。”
“问题是,这些工作怎么体现在对我们的工作评价中?”她问道。
根据国内咨询机构麦可思在一篇文章中的介绍,目前国内高校对辅导员考核评价的具体内容各有不同,但在一些大方向上有某些一致性。
比如,安徽某大学辅导员的考核主要包括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和价值引领、党团和班级建设、学风建设、学生日常事务管理、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工作的岗位职责等10个方面。某师范学院辅导员考核内容则包括德、能、勤、绩四个方面,每个方面又分成若干细则。例如,在“勤”的方面,就包括是否经常组织政治理论学习,是否坚持深入班级、宿舍,乃至是否按时参加院校组织的会议等。
“这些条目看似翔实,但往往流于形式。”以辅导员深入宿舍的要求为例,王兴说,缺乏责任感的辅导员完全可以到各宿舍楼“打卡”后便离开;而对于认真负责的辅导员来说,这项规定反而加重了他们的工作成本。“因为他们在与学生深入交流的同时,还要时刻注意留下自己完成这项工作的‘证据’。”
正是辅导员工作考核标准的模糊性,导致高校对于辅导员的考核往往流于形式,反映在具体工作中,便是对辅导员的考核缺乏辨析度,其工作成绩的优劣很难在校方评价中体现出来。“说白了就是干好干坏一个样。做得好的得不到奖励,做得不好也难以被淘汰。”王兴说。
据他回忆,在从事辅导员工作的10年间,他所在的学校仅有一名辅导员的考核没有达标。“后来,那名辅导员主动离职了。”
也恰恰是因为这种现状,才导致对于已经出现的“非升即走”制度探索,作为“当事方”的辅导员群体普遍“无感”。正如赵晶受访时所言:“如果有一天,我身边真的有同事因为这项制度而被淘汰,我才会觉得有压力。但在目前这种情况下,我不觉得这项制度会改变什么。”
正在扩大的“非升即走”
除了可能给进一步推行辅导员“非升即走”制度带来影响外,缺乏区分度的评价标准对当下的辅导员工作也产生了一定影响。
作为一名有着10年“教龄”的老辅导员,王兴近两年的一个突出感受是——“躺平者”在新近入职的辅导员中变得越来越常见。
“辅导员的工作是很杂的,除了负责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以及一些本职工作外,还要承担大量行政和学生管理方面的非本职工作。”他说,以往面对这些工作时,年轻辅导员的干劲大,热情也很高。但近几年,新辅导员群体的工作热情却在降低。“他们往往只做自己‘分内’的事,很少体现出奉献和责任担当,甚至在下班后都联系不到人……”
这种感觉并非王兴独有,刘江也表达过类似的感受。
也许正是出于对辅导员愈加“躺平”的担忧,在记者采访过程中,几乎所有受访辅导员对“非升即走”均持比较欢迎的态度。有辅导员直言:“作为和学生最贴近、最亲近的人,辅导员如果不合格,对学生的危害非常大。‘非升即走’可以帮我们把好这一关,对学生应该是有利的。”
值得注意的是,除辅导员外,近年来某些国内高校已经开始在其他行政岗上探索“非升即走”制度。比如云南民族大学2023年以预聘制公开招聘27名工作人员,岗位涉及组织部、学生工作处、教务处等12个部门;华中科技大学也在其《2023年度公开招聘辅导员、职员启事》中明确表示,职员按照预聘制引进……合同期满达到考核要求者,聘为事业编制人员。
然而,要解决某些辅导员或行政人员的“躺平”问题,一定要借助“非升即走”吗?对此,操太圣直言:“如果不解决‘标准’问题,此类‘非升即走’很容易停留在形式上,难以触及辅导员以及行政人员管理的实质。”
事实上,即便是在欧美等“非升即走”制度的发源地,这项制度也仅针对于高校教师群体。据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郭英剑介绍,国外高校并无“辅导员”这一职位,但存在专门从事学生管理工作的人员,这些人员被统称为职员(staff),且全部为聘任制。“他们的招聘程序相对简单,且流动性强,如果工作做得不好便可能被辞退,学校也很容易找到替代者。”
“当然,高校不会随意开除一名职员,因为若有任何违反常规和法规的操作,学校就可能被告上法庭。这对学校来说显然‘不划算’。”郭英剑说。
对此,田贤鹏表示,无论中外高校,对于教辅人员和行政人员考核的关键,均在于通过一定的标准制定激发相关人员的工作动力,至于以什么样的形式进行考核,只是方式方法问题。
“目前的情况有些类似于破‘五唯’之初大家所遇到的情形。”他说,那就是旧标准已经被废除,但新标准尚未确立。此时,人们总是会有一些迷茫,至于这些迷茫何时消除,就要看新标准何时真正确立。
采访中,《中国科学报》问赵晶,如果她所在的学校针对辅导员实行“非升即走”,她认为比较合理的考核标准是什么?
赵晶思考许久:“之前学校曾经针对我们能否认清所有学生的名字进行过考核,我觉得这个考核挺合理的。毕竟,如果辅导员连学生的名字都不能全部认清,有点儿说不过去吧……”
《中国科学报》 (2023-08-15 第4版 高教聚焦)